|
http://xiapuv.com 作者|朱昌俊 日前,一则“博主因曾感染新冠被开除”的微博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 5月29日,博主“我是小妖怪”发文称,因自己曾感染新冠,现在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据了解,她在乌克兰读研期间感染新冠病毒,回国后在某机构做俄语老师,得知其曾感染新冠后,被要求离职。她自述自己已做五、六十次核酸检测,均呈阴性。这位博主表示希望社会对新冠康复者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这件事目前只有当事人一方的陈述,具体真相如何,或需要企业方面的回应,劳动监察部门也有必要适时介入调查。但她所陈述的感受,也许并不是危言耸听。 事实上,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两年多来,新冠疫情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变化,但围绕新冠肺炎的歧视、污名化现象时时发生。消除病毒带来的歧视“后遗症”,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迫切。 比如,今年初,网上就出现了把新冠阳性患者称作“小阳人”的调侃。而患者遭遇歧视的案例,仅是付诸舆论的就数不胜数。如据上观新闻在本月初的报道,一些新冠患者康复后离开方舱,有人回家和邻居爆发了线上冲突;有人不解发问“方舱回来怎么成仇人了”;有人因不能参与社区核酸筛查没有核酸阴性证明,就医受阻;有的在散步时,被志愿者喊话:“你不要出来害人呀!”…… 值得注意的是,附着在“新冠”标签之上的歧视、污名化行为,不只是直接针对患者,还蔓延到了一些相关群体。比如,此前吉林援建方舱工人返乡时,遭歧视被骂祖宗;河北沧州某小区的核酸志愿者群里,有人呼吁:“医务人员一律不让进小区……不管是哪个医院的,哪个药店的,咱都不能放他进来”。 此次事件中的当事人,自己是一名博主,能够向社会讲述自己的遭际,但更多的“受害者”也许一直处于沉默、隐身的状态中。2021年初,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的针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后遗症的调查就显示,除了身体上的后遗症,更令人心痛的是,很多新冠肺炎的康复者正在遭受社交孤立、甚至是歧视。 这不仅会引起他们的情绪痛苦,还会导致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抑郁症,甚至自伤、自杀倾向行为。研究数据显示,26% 的康复者有睡眠障碍,23%的康复者有焦虑或抑郁症。而就在这几天,有媒体报道了新冠疫情对公共精神健康的冲击,其中就提到,巴西一项最新研究提出警示:在疫情初期,巴西10-29岁的人的自杀率较预期下降了19%;然而,最年长群体的自杀率上升,因为他们更易受疫情冲击,且因社会限制而更加孤立。 不夸张地说,遏制新冠病毒所衍生出的“歧视病毒”,对于人身心的重要性,可能不亚于防控病毒本身。 当然,针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歧视,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些是显性的,有些则是隐性的。一些人在社交场合会刻意孤立新冠康复群体,一些人习惯了给新冠患者贴上标签,这些尚可被归为道德范畴。但还有一些则已突破法律底线。 比如,早在2020年4月(第一轮疫情后不久),最高法就印发指导意见,明确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劳动者来自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一次,博主自曝因曾感染新冠被开除,如果属实的话,相关企业就涉嫌违法。 值得警惕的是,目前上海等地正处于“解封”前夕,随着复工复产逐步启动,届时是否也会出现员工仅仅因为被隔离,或者被确诊过就被企业开除的现象?对此,企业也要掂量法律风险,劳动监察部门则有必要提前做好普法工作。 当舆论谈论新冠肺炎歧视话题,当自述因感染而被开除的博主呼吁社会对新冠康复者多一些宽容理解时,他们的立场似乎都是代表被歧视的“受害者”说话。其实,防范新冠肺炎歧视,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好少数群体的权益,也是为了防范和修复新冠肺炎给社会精神健康带来的灼伤之必须。它真实地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境遇。 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是,如果对与新冠肺炎相关的群体受歧视、排挤成为一种流行,也意味着,“病毒”和“瘟疫”在人心上扎下了根。每个人在公共生活中都要变得小心翼翼,随时随地提防他人,高度警惕一个莫须有的“敌人”。 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只会人为增加社会的信任阈值和社会运行中的摩擦,让更多人变得狭隘、自私、偏激,而不是包容、开放与理解。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与一些极端的、一刀切的防控措施形成相互强化的效果,最终会令社会防疫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么,告别歧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最关键的,其实仅仅是每个人多一些常识感。谈到肺炎疫情下的歧视,很多人很容易想到桑塔格所描述的“疾病的隐喻”,似乎对流行病的污名和歧视,是人性使然。但这却低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要知道,与麻风、天花、肺结核等流行病大流行的时代相比,今天的网络时代,社会整体的科学素养,尤其是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已经大为提高,只要我们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减少因为“无知”而产生的由恐惧所支配的歧视与排斥。 而公共政策层面,当然也可以做得更多。比如,对康复患者的后期医学观察,更人性化、科学化。我注意到,前述所提到的上观新闻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一名自方舱出来20多天的康复者,其所在的小区已经可以每户轮流申请出门,但她不知道,像自己这样阳过的人怎样才算重获自由,“我们的门磁一直没取过,不确定什么事件算是‘闭幕式’。”当公共政策层面,不能对康复患者有更人性化的接纳和正常沟通,显然就容易助长社会的偏见和歧视。 很多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到疫情前的生活?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但至少,我们可以努力在心态上尽量回归到过去,不自我设限,不增加歧视和对他人的敌视。 也只有告别歧视和偏见,不论现在还是未来,我们也才能真正从新冠的阴影中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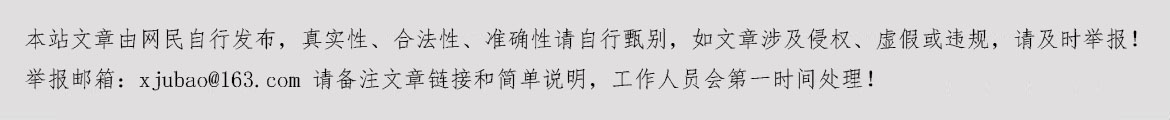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分享
邀请